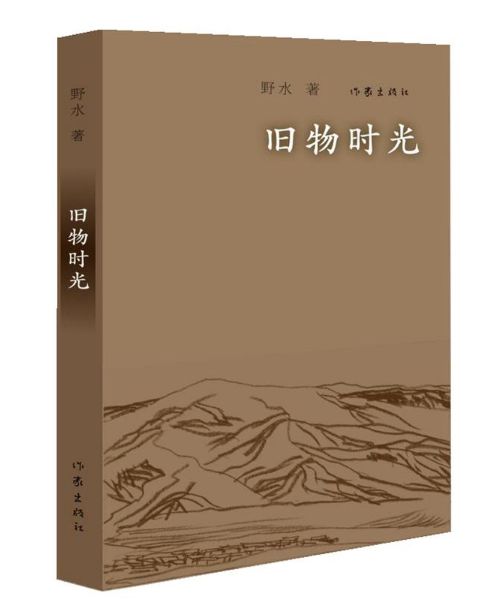野 水 著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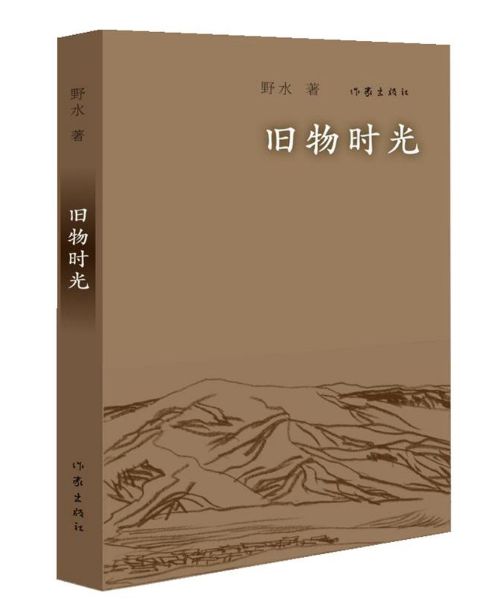
一个行走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人,当他回望故乡山水时,那些凝聚在旧物里的时光,是抹不掉的记忆,是看得见的乡愁。

上次回家,时在清明。我扛起一把锄头,用了将近四十分钟,才锄完了父母坟茔周围的杂草,用手锯锯了几棵松树的股枝便湿透了脊背。姿势的正确无法掩盖体力的不支。清明的天气并不很热,汗水却哗哗地顺脸流淌。我已经不是一个合格的体力劳动者了——我已完全退化。虽然还能分出五谷,但四体不勤却是不争的事实。尽管我每天早晨6点起床,在操场奋力行走一个小时,却赶不上比我年龄大好多,每天跳广场舞的阿姨。眼看着和她们的距离越来越大,没有任何办法。
回到故乡,我已经是一个客人。认识我的人,一般已经人老眼花,除非走到他(她)跟前递一根烟寒暄,他(她)才能认出我来:啊,你回来了,啥时回来的?随之转动烟屁股,眯着眼看过滤嘴上的字,以此鉴别我在外边混得如何。后生们叫叔的我已不认识了,只能从眉眼判断他是谁家的孩子。实在认不出来,问一声你大是谁,孩子才怯怯地说出他大的名字。更可怕的是,现在要问:你爷是谁?我的几个同年,均已胡子拉碴,一脸沧桑,三句话后便无任何可以沟通的主题思想。他们认为我混得好,是个城市人了,岂不知我是一个迷途的老羊,仍想在这山沟里寻觅适口的一把野草。
我已两脚悬空,无法落地。
——野水



野水,原名王茂林,陕西富平人。2010年开始写作,辞赋、小说、散文及评论等体裁作品散见于《中华辞赋》《天津文学》《青海湖》《山东文学》《延河》《延安文学》《北方作家》《奔流》《当代小说》《社会保障报》《人民代表报》《西安日报》《西安晚报》《伊犁晚报》《中国作家网》《陕西作家网》等杂志、报刊和网站。多篇散文被选入各类文集;短篇小说《浓雾》《老鸹》《圣诞狗》分别获得省内外文学杂志年度最佳短篇小说奖。
旧物时光,让回家的路永不荒芜
鲍坚

中国作协会员,中华文学基金会秘书长,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管委会副主任。出版散文集《无非世事》、长篇历史传记《清风有骨》等。
在那个山村,野水是一个农民,从小到大跟随父亲在地里耕耘,收获生命中一日都不可缺少的粮食。离开那里之后,他来到了另一个叫做文学的山村继续当农民,也还是耕耘,这本《旧物时光》便是他的收获。虽然只是丰硕成果中的一仓麦、一筐枣,却足以让我倾心于它们的香和甜,不仅因为那些使人心中悠扬泛波的故事,还因为踈旷的文笔之中值得品味的细腻与优美。
方英文
著名作家,陕西省作协副主席
野水先生的文章醇厚,笔势开阔,有着浓郁的生活气息。

马河声

著名文化学者,书画家
野水内秀若丝,非深交为友而不可知。其文骨内含,故其为文虽短时日而老辣不着痕迹。
理洵
陕西省作协会员,著名书评人。博学善文,以随笔、书评和书画等文艺评论见长。
他写文章,有时署名野水,有时署名王茂林,名字不停歇地换,但不管怎样地换,他文字的好却换不掉。他所写,大多为乡野物什,荒村佚事,但却用情稠密,文字则精雕细琢,很有些见朴见拙的气息,也有乡村隐去的失落的情怀。这样的文字是独特的,亦为极其少见的,但他却不能博得大名,实应为一个时代的悲哀。

王向力

著有中篇小说《续修家谱》《寒尽不知年》《净土》《坚硬的河流》等10余篇。散文散见于《延河》《西安晚报》等杂志报刊。
怀旧不是一味的品咂苦涩,他的每一件旧物件上蓄满浓浓的亲情和爱意。逝去的时光里,你看到另一个完全新奇和陌生的世界,在艺术的展示中,那是一颗灵魂不断高扬的过程。
曲明
拍摄有纪录片、专题片、广告、电视短剧多部,文学及电视节目曾获得专业和行业奖项若干。小说、散文及评论等散见于《山西文学》《北方文学》《广州文艺》等刊。
老屋院里木格子窗的台沿上,是砍刀栖息的地方。
野水的文字有画面,质感十足。请看这段文字:但是,仔细揣摩,对于文字的评介,仅限于技术层面,很难概括他的散文带给读者的强烈震撼。故常常在思考,那文字背后隐匿的,是怎样的一个灵魂?换句话说,是怎样的磨砺与沉淀,让野水的散文,有了不同寻常的厚重与广阔?

时光惊雪 旧物不言
浓郁的西北风情
淳厚的乡土亲情
质朴的人文深情

《旧物时光》章节试读
砍刀的声音是清脆的。它正值青年,有着过人的膂力。盘根错节的灌木完全不能抵挡它的勇气。伴随着咔咔的砍剁的声音,那些粗细不一的股枝在空中纷乱地跳跃,最后都落在地上,架在草丛。空中的老鹰,被激越的声音所激励,将一双羽翼大大地撕扯开来,平铺在苍蓝的天空,像一片轻盈的树叶,飘荡,滑翔。远处一只野兔,探出头颅,小心地张望。它看到了砍刀矫捷的身姿在空中划过的亮光。它撒开两腿,一路狂奔,消失在一片乱草之中,看不见任何踪影,只留下干枯颤动的草叶。微弱的鸟鸣之声,在峡谷的悬崖间被霍霍的砍刀镇压吞噬,之后,那些鸣声像风中的灯焰,齐齐熄灭。孤寂的山野里,只留下砍刀咔咔的声音和父亲吁吁的喘气声。
砍刀
——野水《》
马灯后来进入了好多人的家院,是在各户有了自己的“一亩三分地”之后。马灯是夜间生产劳作照明的光源。夏收之后的麦场里,马灯高高地悬挂在场边的一根杆子上。光影弥漫了周围不大面积的空间,木锨扬起的麦子在空中散乱地飞舞,细碎的麦秸随风飘落在马灯的罩子上。偶尔有从风中分离出来的麦粒打在灯罩上,发出乒乒乓乓的声音。间或,父亲会停下手中的木锨,仰头看看昏黑的天空中是否有风吹过。手拿扫帚的我坐在一边,能从马灯光影的反射下看见那些蹦跳到别处的麦粒。它们小小的身体,竟能在地上投下阴影。那些阴影暴露出它们的所在,我会在起身扫落麦堆的时候,走出很远,用扫帚将它们“赶回”应该呆的地方。但是,过一会儿,我又会从另一个不易窥视的角度看见那些淘气的麦粒,落在了它们不该落的地方——是马灯的光亮暴露了它们顽皮的行踪,如此反复。那些曾经的黑夜,我不但听见了麦粒打在马灯上的声音,而且听到了麦粒落在草帽上的声音。父亲并不躲避那些麦粒的敲击,相反,他喜欢听那清脆的声音,那是他能感受到而且看得见的一种充实。风向在变换,父亲马灯下的身影也在麦场里不时地左右移动。没有风的时间,我们会坐下来歇息,等候。马灯照耀下的地上就会投下两个沉默的影子。因为要等待适于扬场的好风,我们有时会一夜守在麦场,相对无言,直到天亮。
马灯
——野水《》
露野的碓窝,雨天里总是蓄满一池清水,如一汪毛眼静静地看着天空,静谧,沉稳。它的身子已经深深地嵌入土地中了。雨水填满了圆窝,又顺着四周缓慢地淌下来,将它洗得油光铮亮。一俟天空青碧,碓窝里就又发出“咚咚”的撞击声。碓窝里总是用水湿润好的玉米粒儿,青油烤干的红辣椒,脆干的花椒壳子。在渭北,它最忙碌的时候,是在每年的腊月,行将“喝五豆”的前几天。五豆,生之于土,碎之于石,经由碓窝舂出,饱含土的滋润,携带着手工的温热。那时候,婆总是在腊月初五的前两天里淘好玉米。泡涨了,滤去水分,倒在门前擦干净的碓窝里,坐个小木凳子,手里提着沉重的碓椎,一声接一声地砸进碓窝,那声音听起来缓慢而有力;头上的手帕,随着碓椎的起落在风中飘展,显露出脑后纱泡罩着的大大的发髻来。间或,有光溜溜的玉米粒儿从碓窝里飞溅出来,躲进旁边的柴草堆里,婆就摸索着去捡拾,在围裙上蹭去浮土,再放进去。碓椎沉闷的声音便又一声接一声地在屋后的土崖间回荡。
碓窝
——野水《》
一台摆满花馍的什箩,放在村子巷口,那是莲的女儿的婆家送来的祭礼。高高的油塔,肥胖而白的大花卷,纸糊的棉衣棉被,都摆放在莲儿灵柩前的桌子上了。一声炮响,长长的送葬队伍一路蜿蜒而去,直至村子的老坟地;鼓乐喧天,撕裂的哭声穿越了云霄,随风飘落在村下的河谷。什箩里的那些祭品,是供莲儿在冥间享用的,这些丰盛的“大餐”,将使她在黑暗的世界里,不惮于饥饿和寒冷,仍旧延续一颗永不老去的魂灵。这颗魂灵,安详,沉静,一直回望着她当年坐着花轿来时的那条小路……
现在,红漆雕花的什箩,默默地隐居在这个民居的厢房。它已退出历史的舞台。它将自己辉煌的青春,奉献给了那些如当年的莲儿一样青春涌动的女人。此刻,它更像一位垂暮的老人,心如止水,波澜不惊。
什箩,讲述了那些过去的故事。
什箩
——野水《》